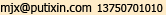| 走出大门,不远便是一条小街,街上挤满了粜籴麦粮和各式各样的交易人物,这种景象,在我的故乡很久不见了,看到不禁一乐!紧走了几步,在一个小食摊前坐了下来,叫了一碗胡辣汤,一碟子煎粉,四个馒头,饱吃了一顿,立时就感到身上暖和和的,精神一振,昨晚的饥寒疲劳,都随之烟消云散了!付过了钱,问清去圣泉寺的道路,我迎着徐徐上升的朝阳,一步一步地又向前迈进!
圣泉寺,为萧县名胜古迹之一。寺址在萧县城西北一座山腰上,寺后和两侧都是崇山峻岭,前面是岱山湖,寺内植有四季常青的花木,寺外周围则被松、柏、李、桃、石榴、梨、枣等树环绕着,特别显得清净幽雅,巍峨庄严,实为不可多得的一所佛教圣地!
寺东石罅中有泉,水清冽而甘美,据说远至徐州的大人先生们,都经常派专人取之烹茶。又,无论是春、夏、秋、冬、雨、晴、旱、涝,泉水永远是不增不减,不溢不涸,保持涓涓细流的原状,由于有这些灵异,所以叫做“圣泉”,寺因为建在泉的附近,也就很自然地寺以泉名了!
我到圣泉寺,正是吃午饭的时分,一说是从保安山来的,寺内的一位老和尚非常客气,一面叫工人给我打水洗脸,一面又叫去厨房用饭,亲切之情,犹如家人,使我十分感激!
饭后,老和尚因事进城去了,由一位青年比丘陪着我讲话,因为彼此都年轻,又是初次见面,默默坐了一会子,都没有找到说话的资料,我正觉得不安,他即拎起我的行李说:“我看你很累,你到楼上去睡一觉吧!”说过,他即把我的行李拿到拱翠堂旁边的一间小楼上去了,我高兴地跟在他后面上去。到楼上他又对我说:“这儿是客房,床铺被褥都现成的,你睡吧!到吃饭的时候我来喊你。”说过他即走下楼去,我也就老实不客气地脱去棉袍,盖上棉被,把头一蒙,呼呼大睡起来。
及至睡醒,走下楼去,那位青年比丘正在拱翠堂的廊下坐着看书,他一见我下来了,即喊工人准备洗脸的东西,并微笑着对我说:“昨晚我到楼上喊你吃饭,几次都没有喊醒你!后来我想你一定是太辛苦了,所以也就不敢再惊动你了!夜里睡得还好吗?”我听了很不好意思地说:“刚才醒来,看到外面的光亮,我还以为天尚未黑哩!起来走到窗前看了看,才知道已经是又一天的早晨了!”他听我这么一说,眼泪都几乎笑了出来,等他笑够了,我们才同进早餐。
吃了早饭,我本想辞行去白土镇净梵寺的,但那位青年比丘却坚持要我再休息一天,他说:“这是老和尚的意思。”接着他又指指天空说:“你看!天就要下雨了,怎么可以走?”果然,不大工夫,霏霏细雨,即淅淅沥沥落个不停!我笑笑对那位青年比丘说:“以前曾听人说: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的故事,现在应把这两句改成: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亦留了!”他听了很高兴。
既然不走了,反正无所事事,也显得无聊;索性向寺内借了一把雨伞,走出山门,独自踯躅在林间的曲径上,静观着湖山烟雨。
此时,湖光山色的本来面目,虽是尽被密云细雨笼罩着了,但是,有时在密云细雨中极目而视,它们若隐若现的姿态,仍然依稀可见。
当微风掠过松柏枝头,把晶莹的水珠,一串串吹落在我脚边的石板上,发出清脆又奇特的声音时,我即感觉到自己好像经行在“七宝行树”之间,有一种“不可以言宣”的滋味,洋溢于身心!
古人说:“秋雨如挽歌!”可是,此时所听所见的秋雨,不但一点也没有像“挽歌”那样悲怆的气氛,相反地,更有助于“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一般的快乐呢!这是古今的秋雨有所不同吗?抑是古人与今人的感官有异?我想了很久也没有得到结论。
回到寺里我同那位青年比丘谈到这个问题,此时我们处得已很熟了,所以他即毫不保留地说出他的看法,他说:“这只是人的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现象,秋雨的本身是不会给人悲伤或快乐的。”接着他举一个例子说:从前有一位学者,最欢喜听雨打芭蕉的声音,他的太太为了投其所好,便在他的书房外面种了几株芭蕉,可是,日子一久,那位学者就感到有点儿厌烦了,于是,即提笔在芭蕉叶上写道——
“是谁多事种芭蕉?
早也潇潇!晚也潇潇!”
他太太见了他的题句,真是啼笑皆非。于是,她也如法炮制,提笔在芭蕉叶上写道:
“是君心绪太无聊!
种了芭蕉,又怨芭蕉!”
你想想看,这不是人的不正常心理在作怪吗?——听他这么一说,使我茅塞顿开。不是么?如果前夜在那间“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的西屋里,落着这样的一场雨,我的感受又将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