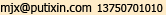| 我在戒期圆满下山的时候,手指和脚趾之间就发现疥疮的“苗头”了,不过尚未严重到影响行动的程度,初到毗卢寺时因为天气冷,也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偶尔痒一阵子就算了,可是,一过年,就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再加上过年时吃点冬菇什么的,不几天浑身生起黄豆般大的紫色脓泡,卧也卧不下,坐也坐不得,痛苦得不可言喻!幸亏大殿上有一位生性慈悲的香灯师,一有空就帮我搭药,不然的话,不说别的,急就急死了!
“有病就应该慢慢地调养,急什么呢?”话虽是有理,一个零丁孤单、穷而且病的人,焉能不急?
说穷,那时的我实在当之无愧!一件棉袍破得如东岳庙的习初所说的都向外流脂油(棉花),一条又薄又短的棉被卷起来时,可能还没有弘一律师在宁波七塔寺挂单的行李卷大。因为他老人家尚有一条破草席子包着,而我则一条草席子也无!至于钱,虽然还没有到我的老师——慈航菩萨——遗嘱上所说的“身无分文”的地步。但是,如果想坐黄包车去街上看看医生,诊断费和医药费不谈,就是车资我也负担不起。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谁把我病的消息传到东岳庙去的。在一个灰濛濛的雨天,我正痛苦得在广单上睁着眼躺着,突然见海秀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走进来,他看到我“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样子,竟放声哭了起来!不一刻习初当家师也来了,见了我就说:“老师弟!你真是自找罪受!如果早听我的话去东岳庙,就是害疥疮也不会这样子惨呀!请你不要再硬啦,我已对这边的知客师讲过啦,马上就同我们坐黄包车去东岳庙。”我无力地摇摇头对他说:“这儿的佛学院办不办还没有一定,我想再等个把月看看,如果真的不办啦,再去东岳庙亲近你!”他听我这么一说,又来火了,他看看房间里没有外人,于是低声对我说:“我住南京十多年了,难道还没有你清楚吗?告诉你吧,你不要再在这边等着做入佛学院的梦啦,这边根本没有办佛学院的消息。你说这边有人去信到宝华山,说这边要请太虚法师办学院,完全是没有的事,即有,也是幌子,招揽你们这班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帮忙帮忙经忏而已,而你这个‘老实头’,就一头撞在南墙上,不知拐弯啦!”
我听习初这么一说,突然使我想到:来毗卢寺的第二天早上,知客、维那和僧值,到我们房间里劈头就问“你们会不会经忏”的话来,哦!我惊讶地叫了一声:“那么我就跟你们去东岳庙吧!”
十二 寄居东岳
入佛学院的梦想既然粉碎了,我只好一拐、一瘸地离开了毗卢寺,而迁移到一向被我认为“环境嘈杂极了!里面糟糕透了”的东岳庙。在走的时候,几位同住的戒兄,似乎比平时待我的态度好了不少,他们都帮着海秀替我收这拾那忙来忙去。其实,我的东西除了一床破棉被之外,只有几本廉价的旧书,有海秀一人收拾就足够,根本就用不着他们帮忙,但他们既然自动来帮忙了,怎能予以拒绝呢?因此,我连说:“谢谢诸位戒兄!谢谢诸位戒兄!”他们也异口同声地说:“戒兄何必客气呢?我们总算有缘吧?不知不觉我们在毗卢寺已共住两个月了,这期间大家虽然曾发生一点点不愉快的事,还不是因为大家都年轻无知吗?现在一听说你要去东岳庙了,我们都很难过!过去的事请你把它忘掉吧,我们后会有期!求学既然没有了希望,不久我们也要各奔前程了!”我说:“是的,我们的确有缘!不然的话,我们相离何止千里?怎么能够同在一个地方受戒,又同在一个地方参学呢?只可惜我们的缘太浅了些,如果缘深,我们能同在一个佛学院读书,不是更好吗?不过,山不转水转,我们只要有缘,如诸位戒兄所说,定会‘后会有期’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完全忘掉虽是不易,然请诸位戒兄放心,我绝对不会怀恨的,但愿清戒兄能原谅我就好了!”说过,大家哈哈笑了阵子,即由海秀替我拎着行李,习初师陪我到客堂告假。出了客堂,我又特别拐到大殿里礼谢那位好心的香灯师,然后就同习初、海秀分坐黄包车去了东岳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