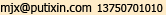| 我躺在广单上,沸腾的思潮,犹如在挹江门外看到的扬子江里遇着大风的急流,汹涌澎湃,滔滔滚滚,一起一落地冲激着我的心,使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想:“这一下子完啦!明天法师把我打人的事传到客堂,知客师父对我的处分可能是先打一顿香板,而后如法师所说的‘遣单’。打打香板也就罢了,假定遣单怎么办呢?回北方小庙吧,有着飞蛾投火般的危险;去东岳庙吧,又有着从丘陵坠落在幽谷样的感触!”就这样展转反侧想了一夜,也没有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他们几个人呢?听了法师一说,好像也觉得事态严重了!一夜穿梭也似的,出出进进向外跑,并且在广单上不时彼此咕咕唧唧地交谈着,大概在研究对策。倒是被打的那位戒兄能沉住气,他只是在刚到广单上睡的时候,呼唏呼唏地叹了几口气,不大工夫,他就心安理得地“梦见周公”去了!
我记得次日正是阴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早粥后知客会同维那和僧值,在斋堂里分配扫塔上供等事宜。分配完毕,其他的都走了,知客师父把我们九个人留在斋堂。随着那位年纪轻轻的,个子小小的,面孔白白的,文质彬彬的,时常笑嘻嘻的维那师父,先看看被我打的那位,腮帮子肿得好像贴着半个苹果的戒兄,然后走到我跟前笑问:“昨晚上你为什么打×清师?”我听了心里猛然一惊,急忙起立合掌,用手指指那位叫什么清的戒兄说:“请维那师父先问问他吧!”论说这样的答复,对常住的执事在礼貌上是不应该的;可是,那位慈悲的维那师父,并不在乎这些,他又笑了笑,既没有去问那位清戒兄,也没有再问我,他即站在斋堂中间,讲了一段内容与昨晚那位法师所说的大同小异的开示,在最后他说:“你们打架的事,大和尚都知道了(消息好快),依常住的共住规约来说,都应该遣单的,现在姑念你们都是初次出外参学,不施任何处罚了。不过,你们要切记:以后不可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否则的话,不仅要遣单,在遣单之前还要重重地打你们一顿香板!”
接着他又说:“马上就要扫塔上供,你们赶快回去准备准备。”说过他就笑嘻嘻地同知客师走了。我们九个人则如获“大赦”似的,走回了住处。在路上我曾这样想:“奇怪呀!为什么维那师父的开示,跟昨晚那位法师说的内容几乎一样呢?难道那位法师已做了我的义务辩护律师了吗?不然,维那师父怎么会对我这个‘侉子’这样子客气呢?因为法师、维那和欺侮我的几个戒兄都是南方人呀,听说南方人是最卫护同乡的,为什么这一次竟成了例外?奇怪!”(摘自《参学琐谈》释真华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