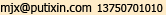|
二 洒泪南行
记得是一个秋高气爽,肃杀气氛非常浓厚的早晨,我背起一个小小的行囊,孩子似的,流着难以控制的眼泪,怀着万感交织的心情,拜别了恩师,踏上了旅途!此时,满山树木的叶子,都已由碧绿而变为萎黄,由萎黄而变为枯黄,由枯黄而坠落在地上,随着凄厉的北风飞舞;而树上所余下来的枝条,却随着风力的大小,时上时下,时左时右地摇摆着,好像在向谁示威,好像在向谁乞怜,又好像在低唤着与它已经脱体了的枯叶!田野里的谷类,如:黄豆、绿豆、黑豆、红豆、秫秫等,也都经过抽芽、生叶、开花、结果的旅程堆进了粮仓。放眼远眺,高山平地,城市村落,无不呈现着荒凉景色,在此时此地,似乎一点有生机的东西也寻不到了!如果硬说有的话,仅是不久前才从又黑又黄的泥土里钻出来的麦苗而已。可怜!那些远看青青一片,近看如针如线一般细小的麦苗,好像不胜其寒的样子,屈曲着头颈,蜷伏在垄沟里,使人看了,倍生凄凉!后来我想想,还幸亏它们这样子呢!不然的话,恐怕早被那些无法无天的野孩子,以及猎狗和羊群踩踏得粉身碎骨了!
河南的佛教,自从一九二七、八年间被“基督将军”冯玉祥破坏以后,昔日清净庄严的道场,在我出来的时候,百分之九十都已成为“古寺无灯凭月照,山门不锁待云封”一般无人住持的破庙了!好一点的不是改为学校,即是变为军营,经像则任人亵渎,寺产则由人瓜分。想想看:在这样的环境下,以寺庙为安身立命的出家人,是何等的惨苦啊!
我出家的小庙,虽是因“地利”(永城是河南最东边的一个县份,而我出家的小庙,又在永城最东边与江苏萧县交界的一座小山上,东南又紧靠着安徽宿县,故素有三不管之称)的关系,成了漏网之鱼,但经过日军、维持会、土匪等八年的洗劫,一日三餐都几乎无法解决了,哪儿还有钱给我作路费?临起身的前一天,东凑凑,西凑凑虽然凑了一些,但算来算去,只够到参学的第一站——南京的一半。为了想节省几文,以备不时之需,在路上遇到有寺庙的地方,我只好老着脸皮去“挂单”。
三
挂单受窘
挂单,亦名挂褡,是佛教里的一种术语。意思是:在寺主的许可之下,行脚僧的衣钵,即可挂在僧堂内的钩上,依止在那儿食宿(后来在参学期间,经验告诉我,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我那时刚离开小庙尚未受戒,不独衣钵全无,而且连挂单的规矩也一窍不通,在这样的情形下,论理是无法挂单的了!但是,我为了解决中途的食宿问题,还是尝试着挂了。好在所遇到的寺主多是宅心仁慈的长老,他们看到我这个青年人,为参学不顾一切艰难困苦的劲儿,大都以同情心打开其方便之门,欣然接待,给与食宿。有的寺主在我与他们辞行时,还特别的送些干粮,嘱我在路上食用呢!
但是,人心毕竟是千差万别的,实难一概而论。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一个人的遭遇,往往因人事的更易而相距悬殊。在我南下参学途中,就曾有过这么一个明显的事例,现在写在下面:
——在一个夕阳返照的傍晚,柔弱而略带些寒意的日光,把人的影子、树的影子、屋的影子,和那些正在低着头啃食麦苗的牛羊的影子,以及许许多多东西的影子,映射得又大又长,大长的程度,使自己都无法认识是自己的了!我——一个为参学而冒着种种艰险徒步行脚的小和尚,背着行李,在萧瑟的寒风吹拂下,踏着自己几乎不认识了的自己的影子,走到一座紧靠在村庄的小庙,目的无非是想在那儿吃一顿,住一宿,第二天一早赶路。
我在小庙门口向里外瞧了瞧:庙是坐北朝南的,门前有个广大的打麦场,庙台子比打麦场高出约五尺左右,全是用土坯做的围墙围着,四周种的尽是些早已脱落了叶子的乔木,光秃秃的,看到就有点儿刺眼的感觉。进门是一间通往佛殿的过道,东西各有厢房一间,房壁也是用坯作成,房顶则是用秫秸,麦秸所盖。用红砖灰瓦合建的佛殿,因年久失修已显得破旧不堪。空阔的庭院中,有一棵老态龙钟的古槐,上面挂满了长短不一的红黄两种颜色的土布,被风吹得飘呀荡的,好像减去了院中的不少寂寥,实际上让人觉得充满了一种“怪力乱神”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