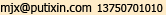行至五台,见一白塔,即礼拜,拜后方知是文殊塔。朝五台后,复向北由桂花城出国,拟往中天竺。一路行去尽是荤食,别无素食可餐,故不能吃,每见树下烂枣累累,捡食充饥。忽有东印土来中国进香之喇嘛,向我问讯,彼此谈话,他云:“来中国三年,欲回本土,因途中障碍太多,不敢妄行,只得折回。”我闻之通身冰冷,即时共辞而别。返回中国,适值隆冬,大雪三尺多深,前不知去路,后无村落,在深雪中过一夜,身寒冰透。余所穿衲袄重十五斤,每下雨雪三五天,坚坐三五日,蒲团下坐成一凹窠,水浸半身,其衣加重十余斤。身幸未伤,一路时与叫化子同睡者,与狗子同夜者。自思既不能往印度,只好回里,化父归佛。主意既定,只身飞跑,直到本乡,拟上家庙住宿,次日再行回家化导,不料将进庙门,适父亦同时进庙,随即礼父三拜。父云:“汝母为汝眼也哭瞎,父亦因找汝,朝山四五处。”说毕即将我蒲团拗归本家。小弟见曰:“父将这邋遢和尚弄到家来作么?”父即曰:“是汝二哥到家。”众乡邻亲属见我回家,悲喜交集。我即令众亲属人等,排班齐整,开导云:“浮世非坚,赶急回头,归心三宝。”劝毕,令各散去。即请父出外上坐,恳切劝导一番。父哭甚哀,我亦同哭。父云:“你要我归依三宝,我必依从你,归依后,但你不能远游。”我即随口答应。父归依毕,余即告以修行路途,旋即向双亲告别,直抵金山销禅堂假,此光绪三十三年春间事也。
进禅堂后,自誓以悟为期,不悟不出禅堂,立行不倒单,不告病假、香假、缝补假、经行假、殿假,宁死在禅堂,不死在外寮,单参念佛是谁一法,不想其他妄念。初住禅堂,规矩不会,从早四板至开大静后,共挨打数百多下香板,毫无烦念,唯念劳动执事,有扰大众,深加惭愧。由是留心学习大规矩小法则,堂内堂外默背透熟。规矩熟后,安心办道,任何人见不到我眼珠,听不到我音声,未见我掉一回头。一日洗澡归,至大殿门,忽掉头向内一望,即被丈室小价诃斥一顿。我见是一小价,惭愧已极,至大静后,打耳巴子七八下,痛责自己。又一日,人问我:“大殿供的什么佛像?”不能答。再追云:“可有胡子么?”亦不能答。因我向未举头上望。一日斋堂受供,工夫得力,举碗不动者,约五分钟,被僧值一耳巴子,打得连碗带筷子一齐下地,衣袍悉沾汤水。此时我仍把住工夫,不许打失(由是迄今,我所住持地方,斋堂不准执事打耳巴子,纵有纠正,须等候初八、二十三、二十四、三十等日)。从朝至暮,日夜精勤,每放香时,东西两单来我位前请示问话,周围一转,广单上下,亦有人围听。至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晚六支香开静櫯子一下,猛然豁落,如千斤担子顿下,打失娘生鼻孔,大哭不止,悲叹无既。自思瞒到今天,沉没轮回,枉受苦楚,哀哉痛哉,无限悲思,叹何能及。次日到班首处,请开示时,前所碍滞之言,悉皆领会。班首云:“汝是悟了语句。”即问念佛是谁?余应答如流。又问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等等问题,随问随答,了无阻滞。未几,和尚班首临堂赞颂,我即搭衣持具,向各寮求忏悔,止其莫赞。一日慈本老人,举手巾作洗脸势,问我:“是什么?”我云:“多了一条手巾,请将手巾放下。”彼不答而退。自此益加仔细,不敢妄自承当,苦心用功,并愿多参知识,以免自大。由是日常修行倍加密切,一听维那报坡,势同抢宝,凡有公务行单各事,置身不顾,操作敏捷,办事精详,为众人冠。至宣统二年春,寺中请余任堂主职,未允。凡外寮行单,上至和尚,下至打扫,所有规矩,无不娴熟。
我在规矩上用心,其义有二:一、当知丛林规矩,为行人悟心大法,见性宏模,现为行法基础,未来为进道阶渐。二、人能留心规矩,巨细清明,毫无讹谬,为己即是立身大本,为人则能拔楔抽钉。我一日往西单尾,有人来我处问话,邻单嫉妒,用醒板打我数十下,维那得知,进堂问我:“阿谁打你?”我即白曰:“是邻单一位师父学打香板,在我肩上试之。”悦众抱气不平,即云:“实是某人打他。”我即曰:“不是。”维那因此未深追究,否则这位邻单师父,必将命送一半,此我学德之密处。故我自用心法,稍得益后,专门学习内外规则,日无倦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