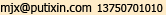传法后,月祖止我他去,侍奉巾瓶,至十六日,复令和尚等悉在床侍奉。十六晚,亲令和尚打二磬,呼我敲小 子,同声念本师释迦牟尼佛。至晚八点钟,招手止念,单呼和尚云:“你向来脾气不纯,对妙后堂,须特加优容,不可苛刻。你可着住外寮,一同护持常住要紧。你们念佛吧。”念约两小时,又招手止念,令我请堂内班首上来,一一向之合掌告假,众人举目罔措。告假毕,请众职回寮,复齐声念佛。约一句钟,复招手止念,握我手云:“你虽接过法,我还不放心,要你发一誓愿,我才放手,若不发愿,我死不放你手。”月祖言毕,不令念佛,候我发愿。我正为难时,月祖又云:“要你讲:愿毕生为高旻尽职。”我踌躇多时,勉强答应,月祖还不放手,又令念佛。至十七日早课下殿,手还未放,渐渐冰冷,我觉骇怕,疑恐不能放开,乃请人双手力推,始放手,只觉如冰冻一块,贴我手上,约五分钟落气,我即为洗澡装缸,此民国十七年事也。
子,同声念本师释迦牟尼佛。至晚八点钟,招手止念,单呼和尚云:“你向来脾气不纯,对妙后堂,须特加优容,不可苛刻。你可着住外寮,一同护持常住要紧。你们念佛吧。”念约两小时,又招手止念,令我请堂内班首上来,一一向之合掌告假,众人举目罔措。告假毕,请众职回寮,复齐声念佛。约一句钟,复招手止念,握我手云:“你虽接过法,我还不放心,要你发一誓愿,我才放手,若不发愿,我死不放你手。”月祖言毕,不令念佛,候我发愿。我正为难时,月祖又云:“要你讲:愿毕生为高旻尽职。”我踌躇多时,勉强答应,月祖还不放手,又令念佛。至十七日早课下殿,手还未放,渐渐冰冷,我觉骇怕,疑恐不能放开,乃请人双手力推,始放手,只觉如冰冻一块,贴我手上,约五分钟落气,我即为洗澡装缸,此民国十七年事也。
至我接住,每有困难事焦愁于心,夜即梦月祖现身,向我多方指示,梦中见到之月祖一如在生时,黄袍白须。彼持杖在我对面,说毕不现。月祖诚不忘高旻,不负佛恩也。余虽接法未久,各事完全一肩担负,惟虑工夫未透,拟再参方。至民国五年,到常州天宁,进堂半日,即承邀请为班首,未允。后高旻来人催回,帮收秋租。至民国六年,复参天童,受后堂职。七年夏,受维那职,秋至福建雪峰,受后堂职,掩生死关。
至民国八年夏,全身水肿,行坐不便,高旻来函催回,函云:“如万一不回,即派人来,路费归我,因果归你。”由是束装来扬。六月初四接位,二十四日,先造柴火房,因大寮不宽,柴草尽堆灶门,稍一大意,火焰上堆,每年到大寮打火者必数次;是以其他一切修造,尚属次要,堆柴草处,最为吃紧,是故兴工,灶外起房一间。又东放生河,上年有人计议,拟为公有,九月初事方暴露,官方先派人来寺查询,限七天答复,否则勘估报领。我在急迫中,各处翻找,忽找得一旧纸包,外批:“内系杂碎纸”,拆开一看,内有门板大的告示一张,系南京总督部堂高、施为高旻寺作放生河之用之布告。又找出此河免钱粮执照一张,心才放下。我即时快函到北京,请至友专函到县,急为出示保护,免夜长梦多,发生意外。七天将到,调查人来寺,即将告示与执照交看。彼等当下无言对答,惟云:“汝有充分证据,回报后听复。”至一月余,北京来函嘱同地方绅董请给告示,卒将文件领得,勒石为志,永禁私人觊觎。于是石碑上墙,永为寺产,诚系铁证,此民国八年事也。
清明扫塔,为僧家顺世之道,我在八年时,探询高旻中兴天慧彻祖之塔安于何处,据我法师明公谈及,天祖塔院在常州扁担河,自咸丰迄今,无人到过。光绪三十四年,楚祖老人往查一次,找三天才寻到,认实无讹,不谓彼处当家否认为高旻祖塔,致楚祖反被他羞辱,扫兴而归。至次年,楚祖复同月朗定祖再去,即将房屋用具各件清单带回。至临行时,月祖云:“不久当择期修复塔院”等语。彼当家云:“汝放木料来,我必阻止兴工,令你原璧归赵。”二老又悲痛而归。自是历代住持,多未闻问。我曾问法师明公和尚,可曾去过?师答:“月楚二位老人去过,尚且不得要领而归,我何敢去。”我闻之心实痛切。余思既为高旻子孙,必当饮水思源,祖塔被人占去,于心何忍。我乃于六月初,带一小价挑供菜篮,直到奔牛,一路问人,皆不知有扬州高旻之塔。找到第三天,顺扁担河东边,望到路边照壁墙外书有磬山寺三字,进内见一新戒礼接,我云:“当家在家吗?”他云:“不在家。”我令他赶快弄饭,并说:“你的当家把我塔院接污糟不堪,今天要同他讲话。”
新戒是前住持之徒,正与现当家不睦,听我说要办他,即将塔院情况和盘托出。饭菜备就,先在塔前上供,我即派小价四处翻挖,不多时,挖出高旻石碑六块。洗清,知是天祖语录后之传法语句。我依旧用土盖好。供毕,当家回寺,我即厉声正色曰:“你当家做什么事,把我塔院弄到这种样子。”当家已得新戒报告:“高旻和尚要办你。”于是急转风头云:“对不起,少迎接。”他即顺住我讲话。我嘱云:“我不能久住,塔院田地山场各件,若有人侵占,或偷窃,你须急到高旻报告。少一分田,我就不答应。”彼云:“请放心。”我又将埋藏之碑重又挖出,令他保存好了。至九月初,该当家与新戒涉讼,二人均离院,因得平安收回。此民国九年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