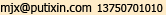|
清定上师隐尘回忆录
(3)
牟秀云
著
高枧乡的人都称我父亲为郑善人。有一年秋天我家的稻谷黄了,请农民去割稻。有一天我母亲见贼割稻子,反而不声不响地避开回到了家。乡亲们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解释说:“俗话说:树活皮,人活脸,树要皮,人要脸,人,谁不要脸皮呢?人,谁自愿作贼呢?都是因为天灾人祸,迫于没有办法,家里穷得无法活,才到我家田里来偷割稻子呀,应该宽容呀!”后来作贼的人知道我母亲如此的仁慈,也被感动得革面洗心,从此不再做贼,成为勤劳为善的跟着母亲学佛的居士,亲友们称我母亲为活观音菩萨,教化人心。
我父母平日就在高枧乡的多宝讲经寺去拜佛,听法师们讲经念经,教化乡里人多行善事。我读大学时,放了寒暑假也跟着父母到寺院里去拜佛、听经、念佛经。期间时常到三门县中学给学生们讲课,当教师。有一年三门县受旱灾,闹饥荒,很多乡里人无法生活。我和父母便拿出家中节存稻谷,一部分分给家里有老人、小孩、断炊的穷人家,一部分借给穷人。到了第二年,高枧乡连受旱灾,欠收,以致上年借谷的人都无法偿还给我家,到我家表示歉意,我父母并不向他们要求偿还欠谷,还招待他们在家中吃饭。当众把乡人们借的债券完全烧成灰烬。对他们说:“我家中节存的稻谷本来是预备受灾时救济大家患难之用的,并不是想囤积图利。现在我把你们欠的债务了结,希望你们不要再放在心上。”过了两年,高枧乡又遇了大饥荒,我父母出尽大量的家产,办理大规模的施粥,嗷嗷待哺的饥民,赖以救活性命的,不下千人。第二年春天,我父母又施出大批的粮种,分赠给贫穷的农民。有人对我父母说:“郑大爷,你救活了很多人,阴德实在太大了。”我父亲回答道:“阴德是阴里作的,只能自己知道,是不让别人知道的,我做的事你们都知道,哪里还谈得上我有阴德呢?”后来,我们兄弟三人都考上黄埔军校,乡亲们都认为是我父亲郑大爷积德的果报。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我父亲信仰佛教,他常说:佛教好,人不学佛,不明理。我父亲去世时,乡亲们听了都痛哭流涕说:“为什么老天爷不让我们替郑大爷死?让郑大爷这样的大善人活着,我们才能生活下去。”当时参加送葬的人很多。郑家的几代人深明佛理,所以在家乡和社会上能力行善事。我们毫无求名邀功之心。
(六)父亲是个佛门弟子
我的父亲名叫郑兴安,是一个信仰佛教、戒“杀、盗、淫、妄、酒”的“五戒”居士。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英、法、美、俄、德、日、意、奥八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是:清政府赔款白银4.5亿两,以海关等税收作保,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活动;清政府拆毁大沽炮台,允许帝国主义国家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增加了新的沉重负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我就出生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战争期间失业的人很多,找一个吃饭的事做很困难。父亲凑点钱开了一个药铺,以祖传中医、按摩针灸的技艺,靠当坐堂中医师来营生。当时人们的信仰门道不一样,有信乩坛的,有信外道的,有信儒教的,有专门愿办慈善的,也有喜欢劝施舍的,虽同劝改恶向善,教化人心,而各人的宗教信仰却都不同。我父亲信仰佛教,经常早晚念佛经,像祖父一样是个修行人,同时又是坐堂中医,终日忙于给人治病。我小时候,父亲常教我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常以佛陀、佛经教化人们,给人们讲述佛陀真理,纠正错误信念,笃信佛教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