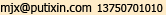| 清定上师隐尘回忆录
(11)
牟秀云
著
(六)母爱如线
小时候,我的体质差,身体瘦弱,隔三五天患点小病,如感冒、发烧、肚子闹病等。母亲听人说:小孩子得病可能与“邪魔”有关。她便打听到有位叫仙姑的比丘尼会“驱邪”。每逢我生病之后,母亲就会去仙姑那儿,然后回来叫我把一只手伸过去,她用根红线系在我的手上。母亲很虔诚叮嘱我:不要去解开它,它会保佑你不害病、不发烧、肚子不痛。于是我随时都小心翼翼,怕把红线给弄断了或者弄掉了。系过几天后,母亲把线从我手上解下来,尔后,她把红线挂在堂屋里供在观音菩萨像的神台上。
中学时,我劝母亲不要信这人。母亲说:“你懂什么?信就灵嘛!心诚,观音菩萨会保佑你的。”上高中时,学校离我家有几十里路,母亲时常要步行到学校来看我,送棉衣、棉鞋、被子,家里做了好吃的也会送我到学校。一次放暑假我回家,母亲正从稻田里回家。母亲见我就喜出望外。“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全山儿病了,现看见我山儿好好的,妈妈放心了。”母亲如释重负地说。我刚进屋坐下,母亲就往堂屋里走,我一边悄悄地看,母亲手捧着红线在拜观音菩萨像。
吃了晚饭,我进堂屋,走到供着观音菩萨像的神台前,我看到神台上的格子系满了密密的红线,我知道每一根红线都有一个母亲爱儿的故事,都有一颗慈母心,都有母亲对儿的惦念和牵挂。我感到那分明就是母亲用心良苦的母爱。
进了大学,每当我平安无事地从广州回到家时,日渐苍老的母亲那份由衷的喜悦和欣慰,总是令人热泪禁不住流下来。我的母亲虽然离我半个多世纪了,今生今世,我知道母爱如线系住我一生的学佛线。
(七)上广州大学途中
1921年我19岁,家乡的人呀贫穷得很,出产的粮食不够吃,又受旱灾、水灾,工人、农民苦得很,生活没法过,有的讨饭,有的逃荒,有的去广州做生意。从广州做生意的人回家常对我的父母讲:“广州大学好,是个培养军事人才的好学校。”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在三门县中学校名列前茅。哥哥郑济时已到广州大学读书了,父母培养两个孩子读大学很不容易,但父母为了把我们培养成才,节衣缩食,到亲友家借钱,支持我报考广州大学。
1921年7月,我考上了广州大学哲学系。那年天气很热。各处闹旱灾,庄稼多半没种上,人民生活艰难。我亲眼目睹全国各地军阀混战,战火连绵,全国人民都恐慌,老百姓逃难,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全国一片混乱。同年9月,我到广州大学上学时,有一天上午,我和几个同学路过离上海十五六里的一个小县城,准备住在一位老乡家,还未进屋,屋顶上落下一发炮弹,这个老乡家的房子全部被炸毁了。幸好这位老乡出门接我们,家里无人,没有伤亡一个人。随后炮弹像下雨一样,在我们的头上直飞,幸好我们逃得快,才保住性命。当时,外国人很欺侮中国人,外国的实力比中国大,他们打出来的炮弹很厉害,炮弹落在哪里,那里便燃起火来,弄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外国人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人,我们逃难时看到一些难民逃难到上海的一个摆渡口,驻守的军队早已过渡,恐怕敌军追来,把河上的浮桥拆了,老百姓在渡口都停止了。这样一来,外国人见人必打。他们以为中国军队在准备渡河,开阵排枪,老百姓像下饺子一样往河里滚,那些逃难的老百姓都惨死在河里,河里飘浮着许多死尸,河水早已被血染红了。那尸首,男的、女的在水中飘飘摇摇的。满是死人血腥气味,我们几个同学正在到广州大学的路上,吓的不得了。走在街上,敌军来了,老百姓都急忙逃命。我亲眼见一个穿粗蓝布衣服的妇女抱着一个小女孩,见敌军追上来了,无法藏身,被迫投到井里自杀了。河边一个中年妇人死在路旁,她那小男孩子还在怀里吃奶。旧中国政府腐败无能,对外屈辱,对老百姓残酷的剥削压迫,中国人民在外国人侵略下、在中国旧政府血腥的压迫下,凄惨的光景简直叫人难以忍受。我从小就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军阀、官僚、地主万分憎恨,对中国人民和自己贫困的父老乡亲十分同情和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