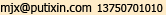|
清定上师隐尘回忆录
(18)
牟秀云
著
(五)壮志难酬,萌生退念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我随着蒋介石从上海撤退到苏州、南京、武汉。1938年夏,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委任张发奎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司兼党政军干部训练团主任,派我担任少将训练处长。当时我顾虑多:因为训练团的学员,大都是从各地区轮流抽调来的军、师、团长、不少人的资历比我高,军级比我高,年龄比我大,我是穷教官,对他们进行训练,他们根本不听。而“训练团”,首先要“整顿军纪”,教育就要摸清楚情况。在干训团整顿军纪中,我发现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贪污成风,层层克扣军饷,使前线士兵隆冬仍穿单衣、盖单被、穿草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唉,以啼饥号寒之师,用劣等武器同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拼,士气何能提高?蒋介石要我搜集几个典型,迅速上报给他。我随即整理了四个贪污严重的高级军官的材料,蒋介石对四个军师团级军官分别给予了降职撤职处分。但是,病树已将倾,岂是除去几条毛虫就能根治得了的。当我再次向蒋介石反映军纪严重败坏时,蒋介石怫然不悦地说:“全山,慢慢来,惩办将领过多,会给共产党攻击我们留下口实!”这时蒋介石斥责我头脑简单,“只知抗日抗日,不知反共防共,消除党国心腹之患……”经此意想不到的训斥,我从内心里才明白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治目的,我开始意识到蒋介石叫得震天响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是欺骗全国人民的谎言。于是,我精忠报国的信念动摇了,对抗日前途悲观了,心里很失望。深感单凭自己满腔热血和振兴中华之心,难酬报国之志,而在这种举世皆浊的社会里,一个人想做到惟我独清,也是十分不易。在进退维谷的彷徨中我产生了隐退念头。
(六)人在军界,心想世人
1940年,祖国大半壁河山失守,中国人民即将成为亡国奴,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苦的阶段,而干训团的“学生官员们”贪污成风,依然花天酒地,中饱私囊。一个个腰缠万贯,吃喝嫖赌,欺压老百姓,抢劫民女,一掷千金。抗日吃紧,而国民党内部很腐败。
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军统局)在重庆枣岚垭罗家湾那个窝荡里,活像一座监狱,前门是“漱舍”,后门在观音岩下的中二路。军统局训练团迁到重庆以后,就选中了中二路罗家湾这个原来重庆市警察警士教练所为局本部和训练团办公地点,后来把隔壁重庆警察局游民习艺所强行占了过来,与中二路杨森的“渝舍”成为邻居。1940年夏季,日军在长江中游大举西犯,攻占了宜昌城,打到了四川的大门口,直接威胁着重庆。接着,日军陆、海、空部队从长沙市、宜昌、广州、南宁、河内等基地出动大批飞机对重庆施以规模空前的毁灭性轰炸,山城重庆在恐怖的空袭警报、敌机轰炸声中颤抖流血、燃烧。当是,我只身随军队来渝,我的家眷留在上海。我借住在浙江同乡、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家,并与李结为无话不谈的契友。一天,我敞开自己的心扉对李士珍说:“士珍兄:这样下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何存?国家和民族危险啊!就拿干训团来说……”李士珍不等我把话说完,便以手指口,示意我谨言慎行,以免惹来杀身之祸,并对我说:“全山老弟,军人要服从领袖,不可谈政治。”我听了李士珍的这番话,使我的心冻成一块冰,真是古人云:“万树梅花一潭水,凶时峰雨旱时酝,君子之交淡如水,醉翁之意不在乎名。”只好“唉!唉!”两声,两人木然对坐,相视无语。在这混乱的社会里醉者多,清醒者少。我想起1937年我回乡探亲,父亲送我返回军营的情景:我们父子俩人相互告别时,我见父亲眼睛发红流下眼泪,我难过地问:“父亲:儿子何事伤了您之心?父亲为何伤心流泪?”父亲擦着泪水对我说:“山儿啊!你我父子两人这一离别,相见就难了。”我对父亲说:“父亲想见儿,有事发个电报,我就回家看您老。”父亲说:“你我各有因缘,我可能再见不到山儿了。”接着父亲教导我:“全山,国事如此,军心民心如此,人民受苦,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儿在外言谨行慎。自古忠孝难全,父已年迈,我们父子见面的机会难得,望儿为国为民尽忠尽孝,今后有疑难不决之事,去找屈文六叔叔……”想着父亲的教导,我的眼泪禁不住往下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