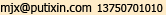行堂,是丛林下四十八单执事之一。干这一单执事的人,大多是“念经是哑和尚,吃饭像俩和尚,打架是傻和尚”一类的苦恼人物。我的能耐虽然比这一类人物好不到哪去,而我毕竟是在佛学院里混过几天,在灵岩山又当过知客的。因此,我进了法雨寺的行堂寮,同寮们对我都是“另眼相看”。尽管我想与他们“打成一片”,但他们却以“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待我。不过在工作方面,他们对我是特别优待的。凡是重的活计:如挑水挑饭等他们都不要我做,只叫我洗洗碗筷,摆摆碗筷,收收碗筷,擦擦桌凳等轻工作。但我个性一向是好强的,我觉得他们对我的这种优待,是可怜我,是侮辱我。也因此,我做了几天的轻工作,就学着挑水(其实,挑水的工作,我在小庙就做过了,只是水桶较小些)挑饭了;也因此,同寮们渐渐对我有了好感;当然,我为了自己能够“胜任”,也感到“愉快”了!
有一天,我挑了一百多斤重的两桶水,上台阶时不慎跌了一跤,水桶摔散了,我也成了落汤鸡,惹得纠察师大发脾气,骂我是:“死人!饭桶!”我的脾气大一向是出了名的,试想:我那能受得了他这种辱骂?于是,我举起扁担来就想揍他,但一转念,自己对自己说:“在这种环境下,怎么可以行粗呢?”
我放下扁担,拍拍身上的水,又拿起扁担来不服气地对纠察师说:“不用一个月,就请你收回给我的封号。”
他见我气虎虎地手里握着扁担,一声不响地走了。又一次他见我挑一担水,跑上数十层台阶,面不改色,气不发喘,又喝斥:“你逞什么能?”
我冷笑一声说:“纠察师父您误会了!我不敢逞能,只是想请你看看‘死人’的本事罢了!”
从那次以后,他就把我看成了他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常常想把我“拔掉”,也常常在背后问行堂寮的人:“那个从前寺来的侉子,脾气那样子大,嘴巴又不饶人,能跟你们合得来吗?”
我问他们怎样答复他的?他们说:“我们都说你很好,但他听了好像很不高兴!”
我叹口气说:“纠察师大概要遣我的单了!”
果然,约莫又过了十多天,知客师把我叫到客堂,和言悦色地让我坐,然后对我说道:“本寺现在的经济情形,好像一泓断了源头的死水,用了一杓少一杓,用了一滴减一滴,不久就有干涸的可能!因此,常住里最近有个决定:‘凡是来本寺新住的人,在三天之内,必须自动离开’,你老菩萨做事虽是很发心,奈何是来寺‘新住的人’(新住的人岂止仅我一个,纠察师的用心,欲盖弥彰)真对不起!请你在三天之内,快去找一个挂单的地方,否则的话,莫怪客堂里事前不通知你!”
这番表面客气而骨子里却十分狠毒的谈话,使我听了不禁战栗不已!聪明的读者可以想像得到,普陀山三大寺之一的法雨寺,经济情形都已像“一泓无源头的死水”了,而我再到哪儿去找挂单的地方?我能再回前寺吗?不可能了!因为前寺那时已有“许出不许进”的规定:去佛顶山,更不必想;因为佛顶山那时也不留单了!怎么办呢?走,决定走。就是出了法雨寺饿死,也不愿向知客乞怜!想到这儿,我向知客师父合了个掌,默默地走出了客堂。
(摘自《参学琐谈》释真华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