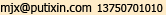参学琐谈 (131)
其次,是我自己见到的一件怪事:
我自从被调任代理文书之后,所有往来文件,多交我办理;办理好,该向上呈的,即叫转呈上级。该往下发的,即往下发。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深夜,领导叫我把一件紧急公文送到上级去。也许是他担心我在穿过森林的时候会骇怕吧?所以临走时,他一再嘱咐我带上武器,以防意外,我笑着对他说:“真发生了意外的话,带着武器更加危险!”
他说:“为什么?”我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武器怎么个用法嘛!”
说过,我即带着公文,只拿手电筒,披上雨衣,出了我们的克难房,踏上唯一走出森林的荒凉小道,朝上级的方向走去。
我们的驻地,距离营部大约有六华里,但至少森林也要占去路程的一半,也就是说;想到送公文的地点,就必须穿过三华里的森林地带。这一段森林中的道路,本来是一条野草没膝、高低不平的荒径;经过一番修整,虽是好了许多,但“荒凉”的景象仍然存在;因此,走在上面嘴说不怕,心里却有三分紧张。到了低洼的地方,好像一下子跌入了幽谷;遇到突起的地方,又像一下子登上了丘陵;同时,老觉得背后有一个人紧跟着,我快他也快,我慢他也慢,而我却始终不敢回头看一下,深恐会被他一把抓着脖子勒死似的。
不料我正胡思乱想地走着,突然眼前觉得一黑,什么也看不见!并且也分不清楚哪是东西南北了!更奇怪的是手电筒也不亮了!一时弄得我成了睁眼瞎子,东摸摸,西摸摸,摸来摸去,觉得一圈子都是树,都是刺手的荆棘,都是齐肩的野草,都是绊脚的葛藤,我愈摸愈急,愈急愈怕,愈怕愈觉得鬼影幢幢,从四面八方向我拢来!
迫切间,脑际突然现出一个念头:“这大概是一般人所说的‘鬼打墙’吧?”这个念头一起,我不再摸索了,也不再骇怕了,我顾不得地下的积水即就地坐了下来,闭起眼睛来休息了一刻,拼命地大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也不知道念了多久,就觉得眼前一亮,随着就有人讲话的声音,接着又是两道刺眼的电光,不一会几个人便到了我面前,我抬头一看,竟是我们单位上的几个兄弟。他们问我:“黑天半夜的又下着雨,你一个人跑到这儿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搞什么玩艺?”我则趁着他们的电筒光站了起来,向四周看了看,都是密密丛丛的草木,也不见路了,于是我问他们:“路呢?路在哪儿?”他们此时大概也觉察到我的神情有点儿不对劲了。随说:“你跟在我们后边走好啦!”
他们带我走了一百多公尺才到了原来我走的那条路上,几个人这才各人来一句“他妈的”口头禅,嘻嘻哈哈地对着我说:“要不是你哇啦哇啦地念南无阿弥陀佛,离路这么远,你在里面坐三天三夜,也不会有人知道!”
我又问他们:“现在几点啦?”其中的一个,看了看他的夜光表,说:“差十分到一点!”
此时,我才惊叫了一声说:“糟糕!我出来的时候才十点多钟,怎么会过得这样子快?”说过,请他们把我送出了森林,我终于当夜把公文送到了营部。最奇怪的是,我一出了森林,手电筒又亮了,亮得比以前更亮!
第二天一早,我回到驻地,单位上正盛传着我被鬼迷路的故事。他们十分关心地详询我迷路经过的情形,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我们的指导员在旁摇着他的尊头说:“在这二十世纪的科学时代,还有什么鬼?”
嗨,真是活该!不到两个星期,这位不信有鬼的指导员,因出外回驻地晚了,竟遭遇到跟我几乎一样的事。所不同的是,我是摸进了森林,而他则是摸进了一圈子围着铁丝网的碉堡。当几个哨兵把他从碉堡里拖出时,不仅吓得面孔发紫,手上和身上也被带刺的铁丝网刺得伤痕累累血迹斑斑。过了几天,一个顽皮的士兵问他:“指导员!你相不相信有鬼?”
他连说:“的确有鬼!的确有鬼!前几天我要不是学着刘复宇念了几句‘南无阿弥陀佛’,恐怕老命怕已完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