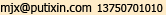参学琐谈 (135)
所学校,叫我服务的一做长桥国民学校,因为那儿的地名叫“万里桥”,所以这篇小文的题目叫做《转业万里》。我到这所学校报到的那一天,正是星期假日;校长、老师们都不在,只有几个小学生在操场上游戏。我走到学校的办公厅前面遇见一个年轻的少女,她看看我没有作声,便走进了一间教室。不一会她又从教室里走了出来,见我仍站在办公厅前面出神,便很大方地问我道:“你哪儿来的?有什么事?”我随即告诉了她,她笑了笑说:“你原来是县政府派来的,那么,请你先在这儿等一下,我去宿舍请校长来。”说过,她就走了。
约莫等了一点多钟,来了一位风度十分潇洒的青年人,他见了我即直截了当地说:“我就是校长。你有县政府的公函吗?”我向他点点头,随把公函取出递给他。他看了看,又说:“很好!”他又指着那位少女对我说:“她也是我们学校里的工友。现在我就把你们的工作分配一下,你不懂的地方,可以问她。”结果他分给我的工作是:敲上、下课的钟,整修校园里的花木,寄送公文、信件;那位女工则担任倒茶、印油印、打扫办公厅等工作。这样的工作大概做了一个多月,校长又命我任收发、写钢板、整理归档文件、晚上看办公厅。敲钟、寄送信件等工作复由女工担任。并且,我除了每月应得的一份薪水之外,又津贴我新台币九十元。于是,女校工看到眼红了,她不止一次地向校长提出抗议,说校长偏心,但校长却一笑置之,不加理睬。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校长、老师们都到凤林看电影去了,我一个人正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突然女校工走了进来,她好像没有话找话说似的,问我:“星期天为什么不到外面玩玩,看看电影,一个人在屋里坐着做什么?”
我抬头看她一眼,随即摇了摇头,表示不愿出去,也不愿意跟她说话。
但她毫不在意地竟在窗前坐了下来,接着像调查户口似地又问:“你是大陆哪一省人?家里还有爸爸妈妈吗?兄弟几个?有姐姐妹妹吗?听说你在大陆当过和尚?真的吗?你当过几年和尚?当和尚能不能娶太太?”
我被她问得又好气又好笑,合上书本,反问她:“你问我这些做什么?”
她笑笑说:“我们是同事嘛!问问有什么关系?”
我说:“问问当然没有关系。可是,我现在正在看书,哪有时间与你话家常?请你到外面去玩玩吧!将来有空再对你说。”说过,我又打开了书本。
她见我下逐客令,倒觉有点儿难为情,然而她坐在那儿仍没有走的意思。沉默了一阵子,她又问我:“听老师们说你的学问很好哩!还看书做什么?你是不是想将来当老师?”
她见我不理不睬,只管看书,于是又自言自语地说:“当校工的人学问再好也不会当老师的!不要再看书啦!出去看看电影,玩玩吧!”
我听了她的话,不禁笑了起来。
她问我:“笑什么?”
我说:“笑你太小看了自己,只要有学校,校工不但可以当老师,当校长都可以。我就是为了想将来当校长,才用功看书的。你不也是读过初中的吗?为什么不继续用功?”
她不信地看看我,说:“好笑!我就没有听说过当校工的人,可以当校长。”
正说着,校长从外面走了进来,他见我同女校工在谈话,对我笑了笑,然后问女校工:“你是不是来请老刘去看电影的?”
女校工娇羞地向校长一笑,一面说“不是,不是”,一面跑了出去。
校长又向我笑一笑,说:“阿×待你不错!”说过,又是一笑,笑得非常的神秘。
等校长走后,我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校长心里在想什么?不然,他怎么会有这种异乎寻常的笑呢?”
(摘自《参学琐谈》释真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