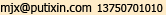参学琐谈 (138)
我正感到奇怪,就听校长问我:“老刘,你怎么啦?”
我说:“没有怎么。”
他说:“刚才听你大叫一声,我吓了一跳!”
我问:“几点啦?”
他说:“大概十二点多了。”
我问:“十二点多了,老师们为什么还不回来睡觉。”
他说:“他们已搬到办公厅去睡了。”
我问:“为什么他们要搬到办公厅去睡呢?”
他说:“因为你呓语连连,他们听了害怕,所以都搬走了。”
我问:“校长!您就不怕吗?”
他说:“刚才还吓了一跳哩,怎么不怕?但是,我再怕也不忍搬走,让你一个病人孤零零地躺在这儿!”
不知道是校长的话触到了我的心,抑是所见境界触到了我的心,我竟莫名其妙地痛哭起来。说也奇怪,不料这一哭,病竟渐渐有了起色。不过,从得病到正式离床,不多不少刚好四十九天。在这四十九天内,大便不是黑血,就是腐肉。那种腥臭之味,自己闻到都想呕吐。可是,好心的校长,和那位好心的女校工,却耐心地替我收拾,替我洗涤,此恩此德,真是使我终生难忘!
二十三 天降至喜
有因有缘事易成,有因无缘法不生;
不信且看寒江柳,一经春风枝枝青!
这首偈子,是一九六二年,我在大岗山上堂说法时所说。学佛的人都知道世出世间一切的一切,都要“因缘具足,乃得成办”的。如果只有因而无缘,或只有缘而无因,终无成就的可能,世间法如是,出世间法亦然,这道理在佛教的典籍中,可说是不胜枚举的。只是因为有些人对这道理没有亲身体验过,不能够死心塌地地信解而已。
我自大病不死之后,即时时刻刻念念不忘再度出家的问题。其实,我这念头在农场的时候就有了,所缺少的无非是个“缘”字。因为万里桥是一个人口不足二百户的偏僻山村,它虽是花东铁路中间的一个小站,如果不是逢年过节,在车站的候车室里是很难看见十个人的。这儿既没有佛教的寺院,也没有天主、基督教堂,甚至一个土地祠也没有。住在这儿的人们,除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外,似乎很少有其它的活动,不但谈不上宗教信仰,恐怕连佛、耶之名,也不知道。学校里的几位老师,都是假时髦的无神论者,他们除了教书,就是去十里之外的凤林镇看看电影什么的,从来就不言及宗教问题;偶尔与我闲聊,即说我样样都好,就是太迷信。校长虽对于释、孔、老庄都喜涉猎,可惜都未能深入,当然也谈不上信仰了!试想: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人,哪儿去获得到一点有关佛教的消息?因此,我怀疑台湾是一个没有佛教的地方,但是我再出家的念头,始终未为环境所左右,也就是说:只要有缘,没有佛教我也要出家。我这种近乎矛盾的念头,在大病好了之后,显得特别强烈。
(摘自《参学琐谈》释真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