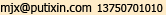|
◎ 旷野的影响——烦恼对心意
在他从乌伯拉加达尼城回来的路上,尊者阿迦曼在沙口那空的诺格拉村过了第一个雨期安居。有许多的弟子,比丘、沙门、在家善信,都欢喜而兴奋于见到他、听到他。这兴奋并不是基于迷信或是个人崇拜,那是他们强烈地热望行善去恶,舍弃鬼神,接受三宝做为他们的皈依处。雨期安居过后,他照常出发游行。这次他前往乌东泰尼城,经过诺布兰弗和巴户区。他一次在巴可雨期安居,另一次在大保区,都在诺格凯城。他在这两个城镇停留了好几年。
尊者阿迦曼住止的地方大都在旷野里,距离每个村落都很远。那个地区人烟稀少,人们遵从并敬重于教导。而旷野真的是荒野,有许许多多的大树,没有人想要去砍伐它们,野生动物在附近自由地漫游着。晚上,住在森林里的各种不同动物的叫声,经常随处可闻。对一个头陀行比丘而言,这种叫声总是感生宁静和悲悯(远甚于恐惧)。这种叫声不像人类制造的声音,它不会打扰他或分散他的注意力,也许是因为这些动物声音里的含义为人们所不了解的缘故。至于人们制造的声音,他们说话或吵闹的声音,跳舞、歌唱和其他娱乐的噪音,传送着可以了解的含义,并感应听者的心,持续地跟随着它们,这在开发禅思期间会分散注意力。如果恰巧这些声音又是由女性所发出的,那就更有害而具破坏性了。没有坚固的定力甲胄,很可能就屈服于它了。这当然不是责怪女性,这只是表明,偶然会发生在头陀行比丘身上的事实。这儿提供他们做为警惕,以便他们在趋向苦灭的奋斗中,能够适当地调伏他们自己。
终其比丘生涯(除了少数期间),长老阿迦曼都处于旷野里。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得到究竟的成就,并且如此慈祥地帮助我们去获得相同的成果。
在他发奋努力的期间,尊者阿迦曼似乎就要被一种慢性而致命的疾病所吞没了,在它凶猛和重复的攻击之下,只有一点点生存的希望。身心都在严格的训练和调御之下,没有一日或一夜不是痛苦地挣扎着,没有娱乐的期望,烦恼和心意微妙的纠缠着,要把心意从烦恼中解救出来是这么困难。一刹那间失去念住,就足以让烦恼再度快速地回扑。一旦烦恼掌握了心意,随着时间的经过,它们的控制就越趋紧密。当烦恼开始放肆的时候,必须恒持警戒,以防它们偷偷地接近和作用,并伴随着予以无情的打击。只有这样做,才能建立起防御线,心意彻底地免于烦恼的掌握。
就在他达到这种程度的安稳之后,他才从隐居中出来教导别人,于是很多人——比丘、沙弥和在家善信——从各方不断地来到,有时候,多得连住的地方都不够。这成了他的负担,他要考虑到他们的福祉和安全,尤其是在家女众和白衣女尼。
有一阵子,他住在乌东泰尼城,巴户区的巴米那永村子里。这地区人烟稀少,充满了野兽,包括老虎,偶尔会到他和弟子们所住的地方来,这对来拜访他和留在那里过夜的人们是危险的。他必须指令村民去搭建高起的平台,高度足以保护躺在上面的人,免得老虎跳上来。夜晚时,禁止他们下来,叫他们备妥器皿或容器,以便身体机能之需。(从远方来的)拜访者不允许停留太多天,因为那个地区的老虎是凶猛而野蛮的,这是村民和比丘们所熟知的。老虎经常骚扰水牛,迫使它们惊慌地回到村子里。有时,在晚上,当他正在专注于经行禅思时,小径的两端用点着蜡烛的灯笼照亮着,他会看到一只大老虎,威风地巡游在成群经过的水牛后面,完全漠视任何人。
在他指导和训练下的比丘们,必须做好应付任何事情的准备。他们住止在旷野和危险的地区之中,没有任何具体的防护或安全。他们必须舍弃虚荣和我慢,视团队中的其他成员如同一身体中的器官。这些是宁静所必需的,在禅思开发期间,它除去了阻隔果证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