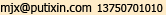我们的心为何徘徊,它为何不静止
现在当我们看见它发生时,因为不了解而可能会质疑:“我的心为何徘徊?我希望它静止,它为何不静止?”这就是以执著之心在修行。
事实上,心只是依循它的本质,但我们却没事找事,想要它静止,并质疑它为何静不下来。然后反感生起,于是又将它加在其他每件事物上,增加自己的怀疑、痛苦与困惑。因此若有伺,就如此省察心里发生的各种事,我们应明智地想:“啊!心就是如此。”瞧!那觉知者在说话,告诉你要如实地看事物。
心就是如此,我们随它那样,心就会静下来。当它不复集中时,就再拿出寻,它便很快地又安定下来。寻与伺就这样一起工作,我们以伺思维各种生起的感觉,当它逐渐变得散乱时,便再次以寻将注意力“举”起来。
这里的重点是,此时的修行一定要以离染的心去做。看见伺与心理感受交互作用,可能会以为心是迷妄的,并开始对它反感。就在这里,我们造成自己痛苦,我们不快乐只因希望心静止。这是邪见,我们只要稍微改正见解,了解这活动只是心的本质,这样就足以对治迷妄,这就称为“放下”。
觉知心的本质就能放下
现在,若我们不执著,练习在活动中离染与于离染中活动,则伺与其它感受的互动便自然会减少。若心不受打扰,伺就会自然倾向于思维法,若我们不思维法,心就会恢复散乱的状态。
因此,有寻然后伺,寻然后伺,寻然后伺……,直到伺变得愈来愈微细为止。起初伺会如流水一样到处跑,若被它迷惑而想要阻止它流动,自然会痛苦。若了解水的流动是它的本质,便不会有痛苦,伺就是如此。有寻,然后伺,与心理感受交互作用。我们可以将这些感受当作禅修的所缘,借由注意那些感受来安定心。
若能如此觉知心的本质,我们便能放下,就像让水流过一样。伺变得愈来愈微细。例如,心也许倾向于思维身体、死亡或其他法的主题。当思维的主题是正确的时,愉悦的感觉就会生起。
那愉悦是什么?是喜,它可能会呈现出毫毛竖立、清凉或轻安的形式,心是狂喜的。喜常伴随着乐,各种感觉来来去去,以及一境性。
心变得愈来愈微细,较粗的特质会被舍离
初禅时,有寻、伺、喜、乐与一境性。那么第二禅如何呢?当心变得愈来愈微细时,寻与伺相对而言便显得粗糙,因此它们被舍离,只留下喜、乐与一境性。这是心自己会做的事,我们无须妄加揣测,只要如实觉知即可。
当心变得更微细时,喜也会被舍离,只留下乐与一境性,那是我们会注意到的。喜去哪里了呢?它哪里也没去,只是心变得愈来愈微细,因此,较粗的特质就会被舍离。只要是太粗的,就会被舍离,它持续舍离,直到达到微细的顶点,即经中所说的第四禅――最高阶段的禅定为止。在此,心逐步舍离粗的心所,直到只剩下一境性与舍为止,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愈渴望安定,心所受的干扰就愈大
当心在修定的阶段时,一定是如此进行,不过这只是让我们了解修行的基本原则。我们想要让心静止,但它就是静不下来,这是渴望安定的修行,其出发点是欲望。
心原来早已受到干扰,接着我们又借由想要让它安定来干扰它,这渴望正是造成干扰的原因。我们不了解这安定内心的渴望就是渴爱,我们愈渴望安定,心所受到的干扰就愈大,除非不再渴望,才能结束和自己的斗争。
若我们了解,心只是根据它的本质在表现,它很自然地会如此来去,对它若不过分感兴趣,就能了解它的方式很像小孩子。小孩可能会乱讲话,若我们了解,就会让他们说,小孩自然会像这样说话,因为他们不懂事。当我们放下时,就不会受他们打扰,而能在小孩喋喋不休与玩耍时,不受干扰地和客人说话。心就像这样,它并无害,除非我们执著它,并被它所迷惑。那才是麻烦真正的起因。
当喜生起时,人们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快乐,只有那些曾体验过它的人才可能领会,乐与一境性都会生起。有寻、伺、喜、乐与一境性,这五种特质都汇集于一处,虽然特质不同,但都集中在一处。我们能看见它们都在那里,就如看见各种不同的水果在一个碗里,可以在心中看见全部的寻、伺、喜、乐与一境性。
若有人问:“怎么会有寻?怎么会有伺?怎么会有喜与乐?”那将会很难回答,但当它们在心里汇聚时,就可以自己去看它怎么会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