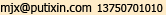|
能海上师传(2)
——谭天 著
如果说,从建筑上来看近慈寺像一个四合院,我没有看到寺庙建筑的全貌,那么20年前的石经寺之行,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寺院。
1985年的夏天,我的父母半强迫地把对佛教一无所知的我,带到了成都石经寺,陪他们去还愿。他们的行为,被当时的我认为是封建迷信。那时,清定法师正在寺里讲经,我也仅仅是去听了一下,就退了出来。我并不知道他是能海上师的第一法子;也不知道1983、1984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曾两次亲临石经寺,并按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之意,将能海上师从西藏学成后,回汉区创建的第一个宗喀巴嫡传密宗道场,由近慈寺还迁于此并设密坛。因为,原近慈寺在文革时已被毁得荡然无存!所剩的便是海公弟子们的坚守,和我所看过的那一个早已不是在原来的地方所修的四合院。
那时,石经寺于我只是有一个传说很灵的肉身祖师,因为当时在祖师楚山坐化处,信众挂了很多“有求必应”类的锦旗。再一个就是寺院内幽静的环境。这也许就是我与石经寺的初缘。而这仍没有脱离海公的道场和他的弟子。后来,无论在拉萨还是在普陀,在我去过的无数庙宇中,石经寺一直给我留有很深的印象,因为它让我知道了佛教的神奇——人可以预知自己的死期,还可以说走就走,还可以肉身不坏!
还有,我已故的母亲,在1980年曾悄悄去朝五台,并在刚刚开始恢复的五台山皈依,却从没有告诉我们她的师父是谁。家人仅仅知道她的法名,皈依师父是五台山显通寺的。她在家看书礼佛诵经,在当时我的眼里,有些神秘。十多年前,当她在成都宝光寺化身院火化的时候,我还不明白她那柔软的心脏,为什么在骨头都化成灰时,还烧不化,为什么寺里的师父说她走得好,因为悲伤已让我无暇他顾。我们遵遗嘱,将骨灰洒在了乐山大佛脚下的三江汇合处,她说:“我要与水族结缘。”
随着时间的流转,我对我的母亲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因而,这次五台之行,我有了特意去寻访她师父的想法。在采访中,我无意中才弄清楚,她的师父竟是能海上师金刚院上座师之一的入室弟子、慧灯堂第四大法子成佛法师,已圆寂。
有意无意中,我所接触的人事物与海公都有如此深的渊源,个中因缘是我所不明白的。
让我欣慰的是,前期的准备和到海公出生地汉旺、圆寂地五台山采访,很顺利地接触到了与海公有关的人与物,使我切身感受到了海公是怎样从一个红尘中人而成为一代高僧的!
常常想,假如很多年后,有人发愿为海公作文学传记,他的情况会比现在更差,材料的收集会比现在更难,因为现在仅存的10来位有缘亲聆海公讲法的前辈们,将全部故去,而无法采访。即使他们是文学大家,也无法像今天的我一样收集到那些宝贵的资料,去采访到海公的弟子及家人。即使这样,在我的采访中,我也深深感到我们已经晚了,无论是他的弟子还是他的亲友,绝大部分的知情人都已故去,而留下的大多都年事已高,对往事的回忆已只剩点滴了。因此,为海公写一本较文学的、生活的、思想的、使读者有身临其感的传记就是当务之急了。当然,这样的描写也需要海公全部生活史料为素材,加以合理的想象和模拟。而我所选择的写法,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传记,多少有着纪实和报道的意味。我想,无论什么形式,只要读者看完此书后能觉得有所获,对学佛生起恭敬之心,我也就心安了。
就海公的史料收集与阅读,我尽了我最大的心力。我想,关于海公的生平任何人欲写他,他们所面对的困扰也将和我一样,那就是海公出家前那段漫长而动荡的个人生活。39年的时间,所留下的只是几乎统一的千余字的文字。他的父母、家世、个人家庭、亲友好朋等等情况几乎为零。由于海公出家后,对在家之事,依佛制早已避而不谈,但就因为如此,才埋没了他前半生很多正确而宝贵的史料,就写传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海公的时代离我们现在并不遥远,但他的史实都如此的迷朦,那些历史伟人呢?可见,要完全的还原一个人是有多么的困难!我将尽力而为之。
我对海公身世的展示,不知我是否能让读者看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海公。
在此书中,我想告诉读者的是,能海上师的一生我们可从两个阶段来阅读:39岁前的龚缉熙,他所表现的是一个自然生命状态下的凡事俗情,追求美好的生活追求精神和理想;39岁后的能海上师,他所展示的则是纯庄严的生命,他舍身求法、依佛制中严厉的戒律来行持弘法,就是因他曾有过一段戎马张扬的生命。如果没有佛家最谨严最规束的戒律,就不足以收敛他宿世的习性,就不足以形成他后来让万人景仰的庄严生命。
我愿意从人的角度来向广大读者介绍他,来看一个平凡生命是如何圆满的。也只有这样,面对他的成就,我们会更加地景仰他,并由此而激励自己。
好了。翻开书继续阅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