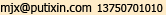3、尊崇《阿含经》精心撰写《学记》
《阿含经》是早期佛教基本经典的汇集,主要内容为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四禅、生死轮回等小乘佛教基本教义。我国汉地佛教,历代多崇尚大乘,故对属于小乘的《阿含经》较少研究。能海上师在初学佛时,也“不识《阿含》大教无上无穷,未肯虚心学习”。但自从到西藏学法以后,就“渐识门路”,开始重视《阿含经》,认识到《阿含经》乃佛亲口所宣,应该好好学习。特别是到了晚年,他更加对《阿含经》备加推崇,“不顾年迈体衰,不怖经多文广”,发誓“一日不死,必学一日”,他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从1960年起,就先后深入细致地学习了《增一阿含》和《杂阿含》等,并根据当年在西藏得康萨仁波切口授的教义,结合自己平时多年的学习心得,撰写《学记》。1962年他完成了《增一阿含学记》,以后又为《杂阿含》续写《学记》。在序文中,他还把《阿含经》的精微义理,看作是佛法的“入门要道”,认为“服膺《阿含》,全心遵行,则神通光明不求而自来”(《增一阿含学记序》)。于此可见其对《阿含经》的尊崇程度。
当时能海上师完成《增一阿含学记》后,待者幻慧师父,有缘抄录了一遍,抄完后恭敬呈还上师,上师笑着说:“此是文殊菩萨亲自点了头的哦!”也就是说已获得本尊印许,由此可《阿含经》的重要!
4、般若为宗重在行持修证
能海上师在拉萨学法时,就特别重视般若。后来历年说法,无不以般若为宗、他曾在一次讲经法会上对大众说:“人家问我们是什么宗派?我说我们的宗派:就叫大般若宗。我们是学般若的,以般若为宗。”他所讲的般若为宗,与我国南北朝时流行的般若学派不尽相同。他之学习般若,重在行持事相,所谓融理于事,于事上显般若。他常说:“般若要从八正道练习显现,方是真般若。盖真谛本无言说,一落言说,即是俗谛,即必须依八正道说也。”他还对“般若”二字作解释:“慧者何?般若也。般若无相,寓于六度万行,故曰慧行。若废行而谈慧,则慧亦无用”。可见他谈般若,意在行持修证,与空谈般若玄理者迥然不同,而是内证般若,外照诸法,最后达到理事无碍,法法圆融的境地。
能海上师的佛学思想很丰富,除上面所讲的四点而外、还有“缘起性空”、“真俗二谛不离”等种种中道观。
能海上师一生弘法,他的佛学思想利益了无数众生,我们择其弘法片段,可见上师的风采。
树近慈家风
能海上师在近慈寺传法弘法,皆依佛制,以戒为本,严格按照教制而行,渐渐形成了严厉的学修体系。
“尊重师承,依戒摄僧”。是能海上师在近慈寺最为强调的。佛法慧命的传续在于师资,能海上师常爱讲他曾受法益的善知识,从张克诚居土到康萨仁波切,无一不提到。上师对自己的亲教师贯一老和尚,五台山的扎萨喇嘛和教《毗卢仪轨》的兴善老喇嘛都有所供养,恭敬礼拜。近慈寺每半月诵戒,上师都要著衣持具去礼拜问讯,生活住处安排都很周密。
上师传戒讲经之前,必先礼师长,然后升座说法,对那些曾给他应酬过师承的法师或老和尚,上师总是迎来送去,恭敬供养,礼拜问讯。他对弟子,不仅施法而且施财,从不吝惜。上师自己每天念经不断,经常讲经,翻译集著,很少休息,还处理寺务接待尼众居士问法,及来访客人,晚上还要修观习定,为法为僧,精勤无畏。他让老比丘收弟子,一则老有弟子侍候,二则有师父负责教管。
近慈寺女居士和尼众除听讲外,太阳落坡以后不准入寺,平时到寺中必须两人以上,到能海上师处问法,上师要求自己的侍者必须在旁边,如果访客要会见僧人,必须在客堂见,不得入僧舍。一次,上师住在昭觉寺,他的长女来告诉他家里生活很困难,上师告诉他说,三宝的财物是不可以徇私的,竟分文也没有给。当时他的侍者因亲生女来谈家常,不便旁听便悄然离去。事后,上师都严厉责备了他,说他有三过:1、不大开房门,2、不高挂门帘,3、不应离开时不别而去。后来住文殊院,有女客来访,谈话中侍者微露笑容,客人离开后,上师责他失戒失威仪。
能海上师自己书写了座右铭:
厚福受享,德性堕落;名誉光荣,我慢加等;
养生优厚,病难更多;顺境安适,般若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