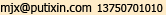我穿过了山门,进了客堂,见了知客师,行了礼,说明了来意,即由一位照客把我送进上客堂。在上客堂刚刚安好单位,一位同道走来向我打招呼,并且一口一个“知客师父”地叫。我一面摇手制止他对我的称呼,一面低声问他:“你老菩萨上下怎么称呼?为什么对我这样子叫?”
他笑了笑,也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反问我:“您不是灵岩山的知客吗?去年我到灵岩山时,还是您问的单哩,您忘啦?”
我也笑笑对他说:“这儿是天童寺的云水堂,而不是灵岩山的客堂,彼此以后还是以老菩萨相称吧?”
我说完,他似乎还想说什么,恰巧此时送我父亲来受戒的海超走了进来,海超看见我就说:“师公!您再不来,他老人家(指我父亲)就要急死了!”我问他:“急什么!”
他说:“昨天从杭州来了一个出家人,说宁沪线铁路也已经不通了,他老人家一听,急得一夜没有睡好,今天早上还含着眼泪对我说:‘如果峻山有个三长两短,我受这个戒还有啥意思?’并且又说‘受了戒马上就回苏州,死也要死在一起’的话。”
我听海超这么一说,饭也没有吃,给上客堂的寮元师打个招呼,就同海超一道看我父亲去了。一路上遇到许多新戒来来去去的,他们看到老戒师父都视若无睹,既不让路,也不合掌。看到这种情形,不禁想起自己在宝华山受戒的情形来,于是我对海超说 “宝华山戒期中严得有点儿近乎野蛮;这儿宽得则有些近乎放纵,宽严不能适中,都会使新戒们手足无措,不知所从!”
正说着,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叫:“峻山!峻山!”我回头一看是我父亲,即喜不自胜地紧走几步迎上去,他老人家也迫不及待地向我走来!
父亲见了我,劈头就问:“听说南京到上海的铁路也不通啦!你怎么来的?”
我对他老人家说:“铁路仍畅通无阻,不然,我怎么还能够来到这儿看你老人家呢?”接着,我就把灵岩山的近况,以及在上海所见到的和听到的一些琐事告诉他老人家,然后问到他老人家在戒期中的生活情形,他说:“由于海超师的照料,在戒期中一切都很好,只是常常挂念着你,昨天一听说铁路不通啦,急得我坐卧不安,恨不得马上就回到苏州看看。现在你来啦,再也没有使我分心的事啦!你坐了一夜的船都没有睡,先回上客堂休息吧!有话晚上再讲。”说罢,他很快地随新戒们向后院走去,海超又陪我在寺内各处看了看,而后我回到上客堂,海超则回到行堂寮,因为他已讨到一个行堂的缺,在为新戒们服务。 (摘自《参学琐谈》释真华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