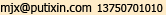第四章 僧团中的生活
从巴利藏经中可以看出,相对于舍利弗、目犍连、阿难等比丘,阿那律比较喜欢安静独处的生活,他不是个积极涉入僧团事务的人。因此,不像上述那些长老,他较少出现在和佛陀有关的传法事件中。
偏好头陀行
从他在《长老偈》的偈颂中也可看出,他和最具代表性的大迦叶尊者一样,非常偏好头陀行①:
托钵乞食回来时,圣者无伴独安居,
诸漏已尽阿那律,寻找破衣做僧衣。
圣者哲人阿那律,诸漏已尽解脱者,
挑捡清洗与染色,然后穿著粪扫衣②。
若人欲贪不知足,喜好群聚易激动,
于彼心中已生起,邪恶染污之特质。
但若正念且少欲,知足并远离纷扰,
喜好独居与禅悦,经常生起精进心,
于彼心中将出现,趋入觉悟之善法,
此人乃是漏尽者,此为大圣所宣说。
五十五年吾遵行,常坐不卧③之苦行。
已经历二十五年,睡眠从此已断除。
阿那律在这些偈颂里提到三种头陀行:托钵乞食、著粪扫衣、常坐不卧,最后是不躺卧,而只在禅定坐姿中睡眠的发愿。在最后一首偈颂中,阿那律暗示他有二十五年完全没有睡觉,也许透过禅定的力量,就能完全恢复心力,所以无须睡眠。但在注释书中提到,在最后一段岁月中,阿那律允许自己有段短暂的睡眠,以消除身体的疲劳。
与善知识讨论佛法
虽然阿那律尊者喜欢独居甚于群聚,但他也并非完全的隐士。佛陀在某部经中说到,阿那律有许多弟子,他训练他们修习天眼。注释书说他游方行脚时,随行弟子有五百名──也许数字有些夸大。
他也和其他比丘以及在家善知识一起讨论佛法,很幸运地,巴利藏为我们保存了其中几次谈话。例如有一次,舍卫国的宫廷木匠五支邀请阿那律与一些比丘吃饭。从其他经典我们知道,五支精通佛法并且致力于修行,因此,在饭后他问了阿那律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他说有比丘建议他修习“无量心解脱”,另外有人建议“广大心解脱”,他想知道两者是否相同。
阿那律回答这两种禅法不同,“无量心解脱”是修习四梵住④──无量慈、悲、喜、舍。但“广大心解脱”则是拓展内心的认知,从有限的范围进到浩瀚无涯的范围;它是藉由扩展遍处的似相⑤达成,即从专注于地、水、色盘等有限的表面范围生起。
与天人谈话
阿那律接着说,有种天人名为“光音天”,他们虽然隶属于同一个天界,但彼此之间的光并不相同,根据他们转生到那个世界的不同禅定特质,所散发的光可能是有限的或无量的,纯净的或有染的。
当有比丘问到时,阿那律证实他所说的这些天人是出自自己的经验,因为他曾出现在他们之间,并和他们谈话。
佛陀的赞叹
另一次,佛陀露地而坐,正对围绕身边的许多比丘开示。然后他转向阿那律,询问他们是否满足于苦行的生活。当阿那律证实这点时,佛陀称赞这种知足,并说:
那些年轻时便出家,在生命的黄金时期成为比丘者,他们并非因怕被国王惩罚,或因怕失去财产、躲债、忧虑或贫穷而如此做。他们过苦行生活,是出于对佛法的信心,以及受到解脱目标的激励。这种人应该如何做?如果他尚未获得禅定的平静与喜悦,或更高的境界,那么他应努力去除五盖与其他烦恼,如此才能获得禅悦,或更高的平静。
在结束开示时,佛陀说之所以会宣布已去世弟子们的成就与未来命运,是为了激励其他人效法他们。世尊的这些话,让阿那律感到非常知足与喜悦。
译注:
①头陀行:“头陀”意指“去除”,比丘因受持头陀行而能去除烦恼,这是佛陀所允许超过戒律标准的苦行。《清净道论》列举有十三支:扫粪衣、三衣、常乞衣、次第乞衣、一座食、一钵食、时后不食、林野住、树下住、露地住、冢间住、随处住与常坐不卧。这些苦行有助于比丘开发知足、出离与精进心。
②粪扫衣:即“尘堆衣”,十三头陀支之一。“扫粪”意指置于道路、墓冢、垃圾堆等尘土之上的,或指被视如尘土可厌的状态。比丘受持扫粪衣,可舍弃对多余之衣的贪着,而能少欲知足。
③常坐不卧:十三头陀支之一。受持此法者,于夜的三时(初夜、中夜、后夜)之中,当有一时起来经行。于行、住、坐、卧四威仪中,只不宜接受床席而卧。修此法可舍离横卧睡眠之乐,增长正行。
④四梵住:即慈、悲、喜、舍四无量。因为梵天界诸天的心常安住在这四种境界,所以称为“梵住”。又因为在禅修时必须将之遍之十方一切无量众生,所以也称为“无量”。慈梵住是希望一切众生快乐;悲梵住是希望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喜梵住是随喜他人的成就;舍梵住是无厌恶而平等地对待他人的心境。
⑤似相:三种禅相(遍作相、取相、似相)之一,禅相即禅修时内心专注的目标。禅修者观察地遍圆盘等时,该目标即为“遍作相”。在观察遍作相后,心中生起与肉眼所见相同的影相,即为取相。专注于取相时,与之类似、更为纯净的一种概念──“似相”就会升起。似相只出现在遍处、三十二分身与入出息念等修法,通过似相而生起近行定与安止定。(摘自《佛陀的圣弟子传2》何慕斯·海克撰)